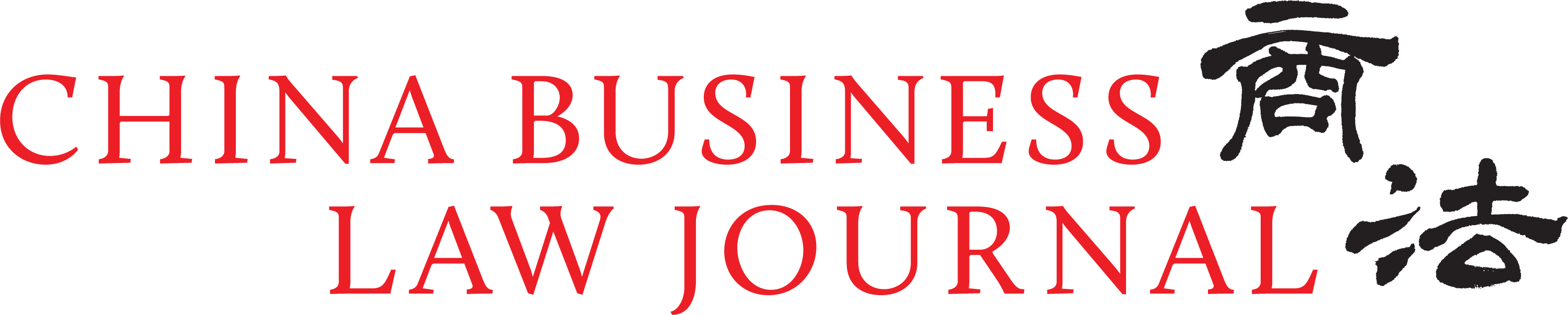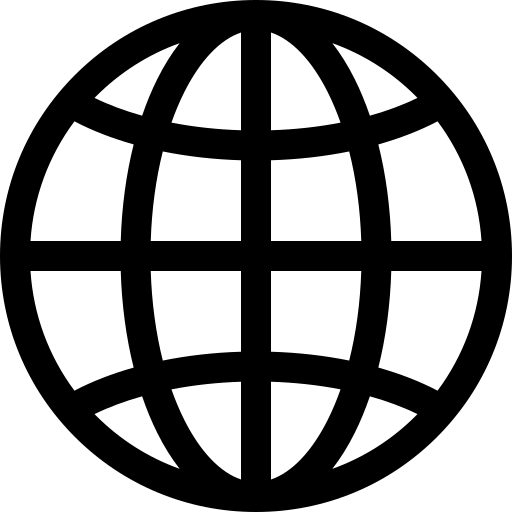基于债权的脆弱性而构建的担保法律制度,将保障债权实现作为基本的立法目的,近年来,立法者愈加关注担保对于改善营商环境的作用。同时,立法者基于作为单务合同的担保合同的从属性、非交换性,也更多地关注担保人利益的保护,比如此前在司法实践中讨论颇多的无效担保制度。
随着《九民纪要》及司法解释的出台,对担保行为效力的判断有了更清晰的认定标准,但关于无效担保的法律后果,即赔偿责任承担问题则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基于此,本文拟从争议解决实践出发,就判定无效担保赔偿责任时的常见问题予以简要介绍和分析。
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前提是担保合同有效,而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则相反。虽然,从学理角度看,两种责任在形式上泾渭分明,探讨的角度也有所不同,但在争议解决的实践中,很多当事人在提起请求时主张的是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担保人也相应地进行针对性抗辩,此时,裁判者如果认定担保合同无效,既有直接驳回当事人请求的,亦有径行依据担保人的过错程度,裁定其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
上述的两种思路在司法实践中都有所体现:在(2021)京03民终14737号二审判决书中,一审法院认定因债权人未证明其就担保人的公司决议予以审查,故对于债权人以履行担保义务为由要求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驳回了该项请求,北京三中院对此予以维持;在(2021)吉01民初1577号判决书中,长春中院在认定债权人未尽到善意、合理审查公司决议的义务后,同时认定担保人等未经公司决议即加盖公章、法人名章,故直接判定担保人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相似的问题在仲裁案件中亦有所反映,如在有的案件中,仲裁庭认为,在双方当事人已经围绕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充分发表意见的情况下,仲裁庭基于对担保合同无效原因的判断,根据过错程度裁定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更有利于高效解决纠纷。
对此,笔者认为,其一,无论是认定担保责任还是赔偿责任,审理核心均在于对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担保责任自不待言,从目前的规则体系上看,《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二款和第六百八十二条第二款,一般性地规定了担保无效时担保人的过错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称民法典担保解释)第十七条进一步将赔偿责任承担比例与过错程度挂钩,将过错程度判断与担保合同无效事由挂钩,与此同时,该条规定又具有模糊性,在大体区分担保合同因自身因素无效和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的情况下,在具体无效事由与过错之间的关系上和具体承担比例上,给予了裁判者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
其二,仅就效率而言,在认定担保合同无效后,由相同的裁判者,结合具体的无效事由判断当事人过错,进而判断赔偿责任承担比例,更不易产生矛盾的情况。如果裁判者在个案中仅认定担保合同无效,而不再就赔偿责任予以认定,则就具体无效事由的分析不宜着墨过多,以防止捆绑另案裁判者的判断。
笔者认为,从目前的争议解决实践可以看出,即使当事人主张担保人承担责任的基础是担保责任,也可在对方当事人就担保合同效力问题提出抗辩时,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应地回复意见,保证双方已就争议的诸项效力事由充分地发表意见,在裁判者认定担保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为进一步就赔偿责任进行判断留出空间。
其三,虽然有学者研究指出,在争议解决实践中,案涉公司因无效担保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实质上类似于有效担保责任,但也需要注意到两者在责任性质和责任范围上的差异。目前一般认为,担保人的赔偿责任属于缔约过失责任,相对应地,赔偿责任范围不受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限制,是以“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为基数,从目前笔者所检索到的裁判书主文表述方式上看,法院一般在明确债务人责任范围的基础上,直接援用民法典担保解释第十七条的表述,裁决担保人承担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几分之几的赔偿责任,而何为“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则是执行法院在对被执行人动产和其他方便财产执行完毕后才能得以明确。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仲裁秘书梁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