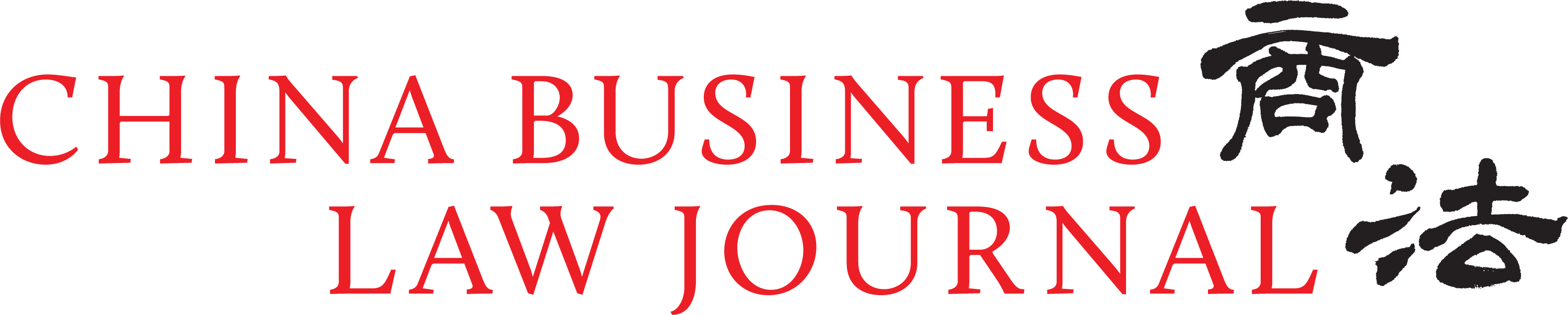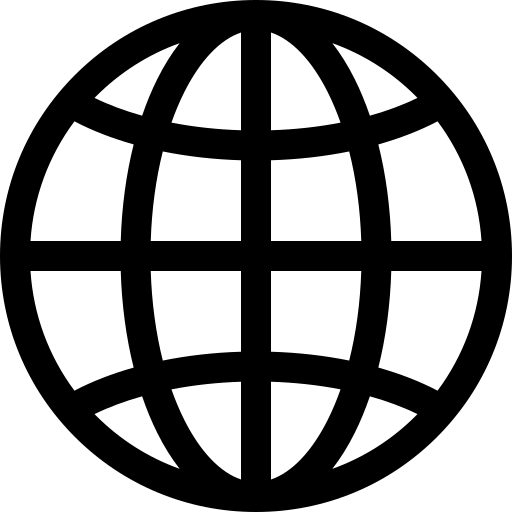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经成为第五生产要素。与勃兴的数据产业相比,数据领域的法律法规稍显单薄,尤其在数据有关权能和权益方面更缺少全局性的明确规定。很多时候,数据被理解为类似智力成果的无形资产,用“贡献度”衡量其受保护的价值,但是数据又天然不是创造的产物,并非一类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
本文将结合国内外立法和司法实践,探讨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构建数据权益保护的可行性及其发展趋势。
有关数据权益的立法

合伙人
通力律师事务所
电话: +86 21 3135 8799
电子信箱:
xun.yang@llinkslaw.com
数据处理者对数据有无权利?如果有,有何权利?数据,究其本源,是以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的信息。然而,“信息”属于民法意义上的物,抑或是知识产权领域的作品、商业秘密?法律避而不言,学界也众说纷纭。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该条位于“民事权利”一章,似乎可以理解为民事主体对数据享有一定民事权利。但是,“依照其规定”是指哪些规定?
2021年生效的《数据安全法》并未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着重于赋予数据处理相关各方保护数据安全的责任,从监管维度保护与数据处理有关的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但是,对数据处理参与各方由于数据处理活动而产生的价值和各自拥有的权益却几乎没有着墨。
2022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与《数据安全法》不同,该意见创新性地提出了公开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的三分法以及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的三权分置。
事实上,意见隐含了立法者解决前述问题的基本思路。数据作为一种信息的集成物,维护数据安全必然会与保障人身权益、财产权益交织在一起。所以,只有区分数据,才能确定适用何种法律以规制数据处理活动,这是破除数据安全保护迷局的第一步。而第二步就是针对数据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参与者,赋予不同的权利。从意见的规定来看,数据资源持有权等权利具有财产权的特征,但并非所有权或其他物权。这可能是考虑到物权具有排他性,而数据的公共性使这一特性难以实现,立法者的缜密可见一斑。

律师助理
通力律师事务所
2023年3月27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浙江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下称《登记办法》),试以另一种全新的方案直接解决前述问题:对依法收集、经过一定算法加工、具有实用价值和智力成果属性的数据,数据处理者可以申请登记知识产权。此种知识产权与著作权等并无显见区别,权利人可以将其作为质押、交易的标的,也可以许可他人使用。
为避免和数据主体权利的冲突,在申请前,数据处理者必须对数据进行匿名化、去标识化,确保其无法还原为原始数据,保护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安全。而且,数据主体也可以在公示期间提出异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至今,浙江省的数据知识产权制度业已初具雏形,登记程序、权利行使、监督管理等规定相对完善。但是,《登记办法》更近似于一种操作规范,对数据知识产权性质及内容的探究尤显不足,这就导致数据知识产权的设立在法理上存在诸多问题。
数据权益保护的司法实践
近年来,因数据收集、处理引起的纠纷层出不穷。法院的裁判理由大多基于商业秘密保护或反不正当竞争。
(1)基于商业秘密保护
商业秘密虽然在法律性质上不是一类“知识产权”,但通常作为类似知识产权的客体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下称《反法》)保护。实践中,在不少数据有关争议中,数据被作为商业秘密获得保护。
在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1)粤0115民初16941号民事判决中,法院认为:首先,涉案文件包含客户名称、联系方式等信息,不易为公众所知悉;其次,原告提交的订单等材料证明涉案文件具有商业价值;再之,原告通过数据安全系统制作表格,并要求员工承担保密义务,足以证明其已经采取了保密措施。所以,涉案文件符合商业秘密的非公知性、价值性、保密性的特征,被告侵犯他人的商业秘密,应赔偿损失。
该案是一则典型的从商业秘密的角度维护数据安全的实例。商业秘密和数据存在共通之处:根据《反法》第九条,商业秘密是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而数据则是表达信息的原始素材。可见,商业秘密与数据的本质都是信息,具备法定要件的数据可以被认定为商业秘密。进而,非法获取、处理数据也是一种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因此,法院可以援引《反法》中保护商业秘密的规定。
当然,数据作为商业秘密保护具有局限性。尤其是,很多数据源自于公开渠道(比如有价证券价格信息),其秘密性很难达到商业秘密保护的要求;有些数据只有公开才能实现价值(比如实时交通信息),其不适宜采取保密措施。这些数据不适宜作为商业秘密保护。
(2)基于反不正当竞争
部分数据权益案件中,涉案数据不能被认定为商业秘密,法院适用《反法》的一般性规定给予裁判。在此类案件中,法院往往会主张数据(产品)为当事人带来了经济利益与竞争优势,非法获取、处理数据的行为破坏了当事人的竞争地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该些案件没有认定对数据的绝对“权利”,而是认可数据控制者对数据拥有的相对的竞争性“权益”。
在(2018)浙01民终7312号淘宝诉美景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认可原告应当对其享有独立的“财产性权益”。法院之所以采用“权益”而非“权利”,主要是因为数据并非知识产权的客体,亦非民法意义上的物。唯有使用“权益”,方能在不违背物权法定原则的前提下,为保护原告利益提供正当理由。另外,法院还指出,涉案产品为淘宝带来了竞争优势,而被诉行为显然损害了该竞争优势,构成不正当竞争。
除了电子商务平台,社交平台也是数据产业的重要参与者。2022年,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民终3789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指出:网络数据有可集成、可交互的特点,平台经营者应当容忍他人合法收集、利用已公开的数据;即,以公开与否为基准,将数据区分为公开数据和未公开数据。透过该判决,法院意图传达的原旨是数据保护从来不是一刀切,而是在鼓励技术创新与进步的目标下,针对不同种类的数据,提出不同的保护。
可行性与展望
采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数据是否可行?诚然,数据知识产权制度可以根本性地解决数据权益归属与保护的难题,从而激发数据潜能,探索数据要素的应用方式,扩展数据市场。但是,数据与其他知识产权客体存在显见的差异,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在法理和实际应用上仍然存在一定困境。
知识产权具有排他性,是一种合法的垄断,这意味着权利人有权禁止第三人收集、处理其已经获得垄断权利的数据。但大量没有采取任何保密措施,也没有设置访问权限的公开数据,已经具有了“公共物品”的特征,这种对数据的排他既不合理,也不现实。
如果赋予了数据绝对垄断的地位,必然导致数据资源集中在少数主体手中。与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不同,数据并非创造的产物,而天然具有原始和公众的属性。若采用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形式,极有可能造成数据垄断,进而导致数据分析应用来源的枯竭。这样对数据权益的保护,不仅未激励市场创新,反而造成了数据产业发展的障碍。
如果在数据权益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上,规定合理使用制度,作为对数据垄断的限制,那么,这些合理使用如何界定?这些合理使用与司法实践中《反法》下的“竞争”关系分析有什么异同?对数据的合理使用,是否存在普适的规则?
与传统知识产权制度的框定维度类似,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必然需要考虑控制者、使用者和公众利益的平衡。既要赋予数据原始拥有者、数据形成过程中的参与者一定的权益,甚至近乎垄断的权益,又不能扼杀数据的流通,允许和鼓励数据被更广泛地应用。
杨迅是通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他的联系方式是电话+86 21 3135 8799以及电邮xun.yang@llinkslaw.com;严怡是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