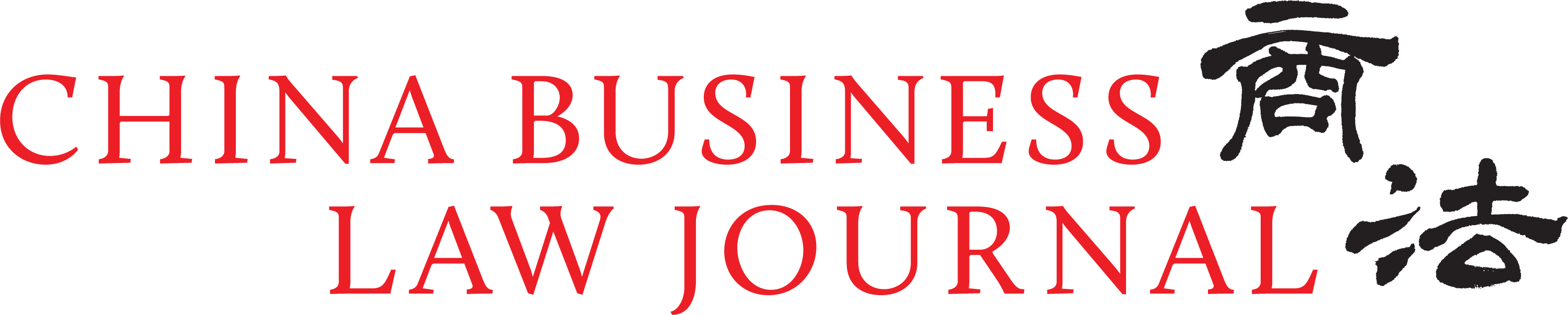中国仲裁界2016年的重大新闻中至少有两件涉及“仲裁地”:其一是深圳国际仲裁院颁布的《关于适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的程序指引》;其二是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贸仲香港)作出的一份裁决。
“仲裁地”事关仲裁裁决的国籍,关乎仲裁协议的准据法及效力,决定了仲裁程序的准据法;还是撤销程序的地理依据,以及适用《纽约公约》的前提。所以仲裁地是仲裁法特有的、基础性的概念之一。英国《1996年仲裁法》将仲裁地定义为juridical seat,这体现了国际仲裁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重大进展:仲裁地不再单纯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连接仲裁裁决与仲裁程序的法律联系。

TIM MENG
金阙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
Managing Partner
GoldenGate Lawyers
“仲裁地”与仲裁机构所在地固然关系密切,但是仲裁机构所在地并非当然的仲裁地。仲裁的实际做出地点往往与该裁决在法律上具有更密切的联系。
国际仲裁实践中,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一些规则(比如UNCITRAL、ICC仲裁规则)规定由仲裁庭结合案件的各种因素确定仲裁地;另一些规则(比如LCIA、HKIAC、SIAC仲裁规则)还是将仲裁机构所在地认定为“仲裁地”。
中国《仲裁法》尚未对“仲裁地”做出明确的定义。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第283条以及《仲裁法》的结构,可知中国大体是按照仲裁机构所在地来确定仲裁裁决的国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各主要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均是将仲裁机构所在地定义为“仲裁地”。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香港仲裁裁决在内地执行的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2010年最高院在DMT一案中做出的复函,都是在实质上以做出裁决的地理位置,而非相关仲裁机构所在地,作为界定裁决国籍的标准。这与《纽约公约》以及中国加入该公约的决定是一致的。
在众多国内仲裁规则中,深圳国际仲裁院颁布的《关于适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的程序指引》是个例外。它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仲裁地为香港,除非仲裁庭另有决定。”这意味着,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凡是适用UNCITRAL仲裁规则、由深圳国际仲裁院管理、且很可能是在深圳做出的仲裁裁决,其国籍默认为香港。
但是人们的疑问是,香港在形成这样一份裁决的过程中到底能起怎样的作用?深圳与香港地理接壤,或深圳国际仲裁院与香港仲裁界保持密切交往,是否足以构成一个充分的法律联系?细心的人士还会发现,UNCITRAL仲裁规则规定,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仲裁地本应由仲裁庭决定,而不是仲裁规则默认的地点。
去年还有一项法院判决值得关注。在该案中,意艾德建筑师事务所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贸仲香港于2015年11月作出的一份仲裁裁决。这原本是中国法院诠释“仲裁地”这个概念的绝好机会,但是南京中院在认定过案件基本事实之后,就直奔结论:“本院经审查,涉案裁决亦不存在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情形,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第一条、第七条之规定……”。
南京中院的行文非常简约,完全没有理睬贸仲2015年版《仲裁规则》关于香港仲裁的特别规定、香港《仲裁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香港仲裁裁决在内地执行的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最高院2010年在DMT一案中做出的复函等一系列法律文件。该判决,尽管结论正确,根本没有讨论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的前提,完全回避对贸仲香港裁决的国籍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总之,缺失对“仲裁地”的定义,不仅会影响中国法院判决的完整性、专业性和公信力,甚至还会造成一些混乱。故此,中国仲裁要走向国际,就必须在立法或者最高院司法解释的层面进一步明确仲裁地这个概念。
作者:金阙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孟霆。其联系方式为电话 +8610 5870 2028 ;电邮 tmeng@goldengatelawyer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