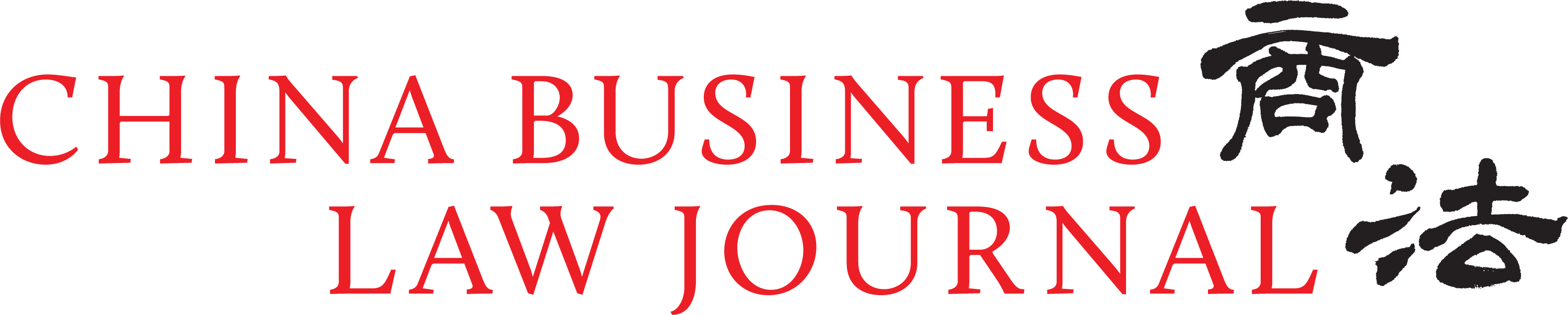行政协议的类型与范围是困扰法律共同体多年的难题,迄今依然没有一个公认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行政协议的类型与范围直接影响了其是否符合仲裁的受案范围。《仲裁法》第二条和第三条分别规定了纠纷可仲裁性的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既凸显了仲裁制度的民间性和社会性,也区分了通过社会权力解决纠纷的仲裁机制与行使国家纠纷解决职责的司法机制。仲裁只能解决社会领域内的纠纷,而无权涉及行政纠纷,否则将使社会权僭越国家权力,甚至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决断。《仲裁法》对案件可仲裁性的规定牵涉司法权的范围及其行使,其性质为强制性规定,其被违反的法律效果是导致仲裁裁决被撤销。
《仲裁法》第三条第2项明确将“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排除在仲裁受案范围之外。在行政争议中,《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11项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排除了仲裁适用于行政协议的可能性。但是,行政协议到底是什么以及包括哪些类型,因理论界与实务界基于不同学科和专业带来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惯性的差异,争议沸沸扬扬。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行政协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行政协议的定义和类型,并规定了因2015年5月1日后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的纠纷,适用《行政诉讼法》。其第二十六条还规定,行政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
然而,争议并没有因此尘埃落定,司法实践对行政协议的认定不仅裁判标准未完全统一,甚至还截然相反。如《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二条第3项将“矿业权等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协议”界定为行政协议,在文义上引申理解,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也应为行政协议。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却将其界定为民事合同,自然可以适用仲裁制度。在《行政协议司法解释》出台之前,一些裁决认为其为民事合同,而可以仲裁解决相应纠纷,如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特78号民事裁定书;一些裁决则认为其为行政协议,不属仲裁范围,如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4民特4号民事裁定书。《行政协议司法解释》颁布后,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规则,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应排除在仲裁范围之外。
尽管如此,行政协议的法律难题并没有因此真正解决。原因在于,《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界定的行政协议类型并不妥当。笔者认为在某些领域的行政协议可界定为民事合同并适用仲裁解决,原因如下:
首先,在中国,行政协议的类型界定首先受价值观念的影响。行政协议的出发点之一是,公益事业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引入市场价值可以有效克服行政机关效率不高、专业不足等沉疴痼疾。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充分认可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在这种背景下,至少适合通过市场配置行政资源的领域,如国有自然资源出让、国家与社会资本合作领域,完全可以也应当适用私法合同机制。
其次,区分行政协议与民事协议的首要标准,应为行政机关缔约时的身份到底是管理者还是民事主体。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迅猛扩张,使国家成为市场交易中最大的买方和卖方,行政机关的市场主体身份也因而越来越重要。区分行政机关缔约身份的最重要标准应是协议的标的:若标的为市场交易客体的,如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使用权,应界定为民事合同。
目前对行政协议的类型化法律作业还存在很多难度,这不仅因为争议聚讼盈庭,还因为行政机关的职责内容与行使方式在不断翻新。可以考虑如下四种类型:一是行政机关与适格主体依法签订的授权后者行使部分行政权力的合同;二是行政机关内部订立的行政协议,如以完成特定工作量为标准的奖惩合同;三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与相对人订立的协议,如征收补偿协议,其未必是双方真正的合意的产物,但具有合意的外观;四是不同行政机关之间订立的行政协议,双方的目的均为实现行政目标,如省际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议。
鉴于行政协议的类型对仲裁影响巨大,加之目前的司法界定未必妥当,值《仲裁法》修改之际,可考虑在《仲裁法》第二条增设一款“机关法人作为民事主体与其他民事主体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以适应中国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谢鸿飞。北仲仲裁秘书高壮对文章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