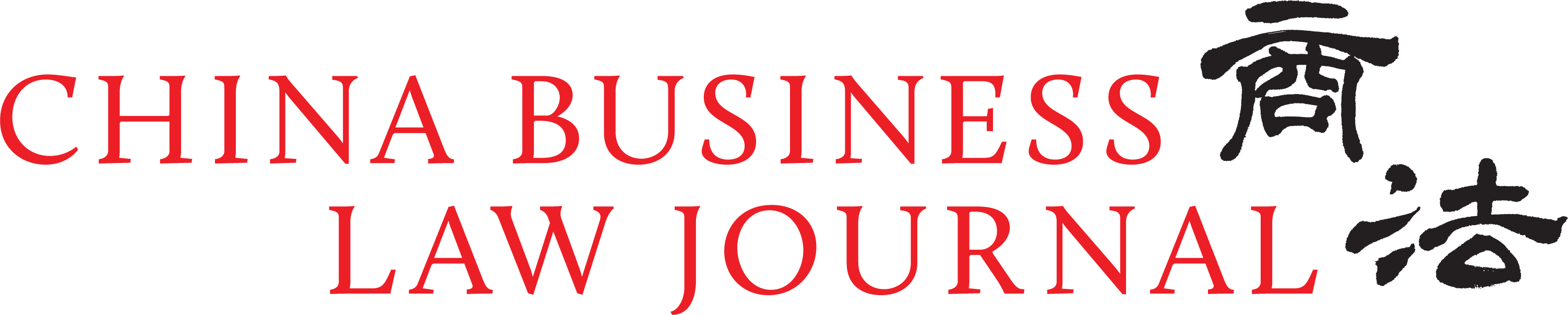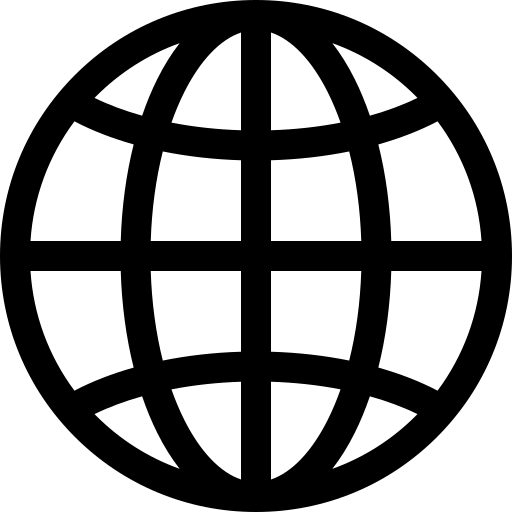虚假仲裁与虚假诉讼并无本质不同。但因仲裁庭/仲裁机构缺乏法院所具有的调查权和惩戒权,企图利用仲裁程序达到特定目的者屡见不鲜。我国法律对于“虚假仲裁”尚无明确定义。一般认为,“虚假仲裁”并非一个法律术语,而是对一种现象的概括。
读者可以参阅《刑法》第307条;《民事诉讼法》第112条、123条;《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以及《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9条。
最高法《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中总结了虚假诉讼的一般要素,其中包括:(1)以规避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2)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3)虚构事实;(4)借用合法的民事程序;(5)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打击虚假仲裁是个难题。《仲裁法》第58条、《民事诉讼法》第237条并未赋予利害关系人仲裁程序异议权、仲裁裁决撤销权和不予执行申请权,也没有赋予国家机关审查调查权、处理权。

金阙律师事务所
管理合伙人
2018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法《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九条第一款首次提出:案外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的,应当提交申请书以及证明其请求成立的证据材料,并符合“有证据证明仲裁案件当事人恶意申请仲裁或者虚假仲裁,损害其合法权益”这一条件。该规定创设了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的制度,标志着虚假仲裁问题步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新阶段。
辨别虚假仲裁并不似想象得那样简单。虚假仲裁中的事实和证据往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比如,在某一案件中,双方系关联公司,在一栋办公楼里办公,一方为制造商,另一方为经销商。经销产品为常见的电子元器件,每件价格在十几元至几百元之间。制造商针对经销商提起仲裁,声称若干年前,经销商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欠付数千
万元。
制造商举证颇为详尽,除了合同、订单统计、和解协议、律师函之外,还提供了几千页的发货单、发票,但是制造商并未对这数千页的文件进行统计说明,甚至连页码都没有。而经销商对这些文件的真实性却一概确认。在首次开庭的时候,经销商连律师都没有聘请。
仲裁庭面对的情况是:对于数年间发生的成千上万单交易,双方都声称根本就没有签署过订单(尽管有订单统计)、没进行过盘点、没进行过结算;制造商在达成和解协议之前,也从未以书面形式追究过经销商的责任。更有甚者,双方都拒绝提供支付凭证和支付统计。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双方就达成了和解协议,确定了赔偿
金额。

金阙律师事务所
律师
另外,双方在仲裁程序启动后以及第一次开庭后又反复达成和解协议,其通过仲裁程序确定赔偿金额的意图十分明显。而且,经销商连诉讼时效这样简单的抗辩意见也不曾提出。面对如此案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仲裁庭恐怕都会对双方进行仲裁的真实目的产生
怀疑。
实务中类似的情形并不罕见。通常,当一个案件同时具备如下几个因素中的数个因素时,虚假仲裁的可能性就很大了:(一)当事人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二)交易活动本身有悖常识,严重违反商业理性。这是虚假仲裁最本质的特征;(三)虽有模糊的证据链,但是缺乏关键性证据,而且证据之间缺乏呼应;(四)双方热切希望达成和解;以及(五)双方并无实质性对抗,仅有象征性的答辩。
在国际仲裁中,常以缺乏“实质性纠纷”和“实质性对抗”为由驳回类似仲裁请求。寻其源头,《纽约公约》(第二条第一款)、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七条第二款)等均要求,“争议”或“分歧”是启动仲裁程序的前提和仲裁程序存在的意义所在。这些条款更多是起到澄清的作用而不是限制的作用,但也揭示了仲裁程序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实质性争议,而绝非简单地要见证双方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
可喜的是,近来中国法院也在若干案件中以仲裁应以双方之间具有“实质性对抗”作为判决的基石,而不再拘泥于以“证据不足”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
孟霆是金阙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他的联系方式为电话 +86 137 0116 4046 以及电邮tmeng@goldengatelawyers.com
晏雪梅是金阙律师事务所律师。她的联系方式为 +86 135 5232 2082 以及电邮syan@goldengatelawyer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