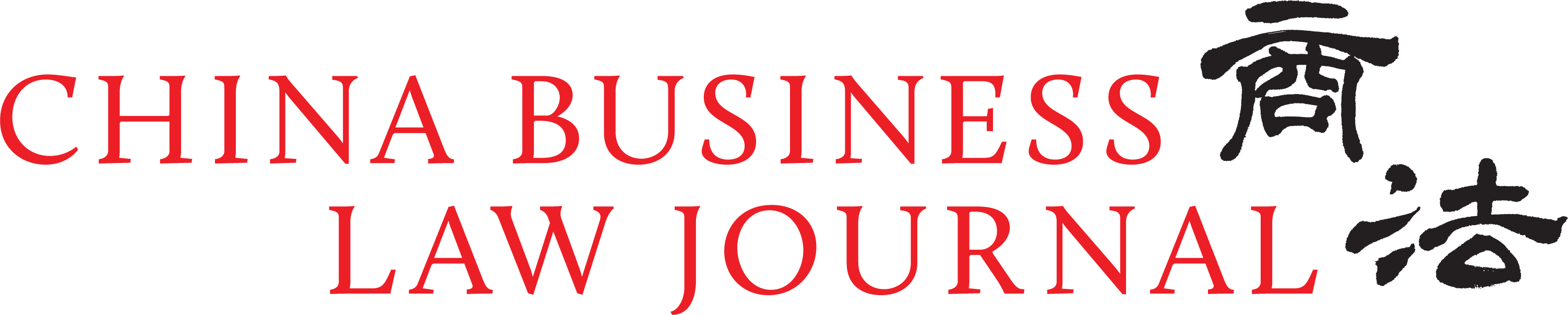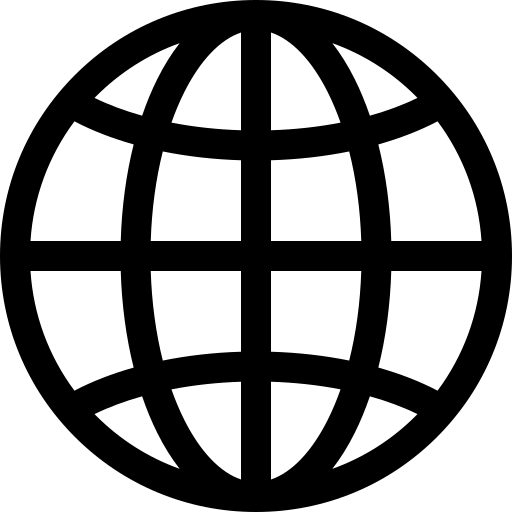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高院)2016年在某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国公司和其经销商之间的垄断纠纷管辖权异议案中作出终审裁定,认为在垄断纠纷涉及公共利益,且中国法律未明确规定其可仲裁的情形下,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不能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该案被称为中国“垄断纠纷是否可仲裁第一案”,江苏高院在该案中的关于“垄断纠纷不可仲裁”的认定一度被认为目前中国司法实践认为垄断争议不可仲裁。对此,笔者认为,垄断争议在中国是否可仲裁仍应个案分析。

HUANG WEI
天元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Managing Partner
Tian Yuan Law Firm
江苏高院关于“垄断争议不可仲裁”的结论与案件背景紧密相关。作为前述案件中被告的代理律师,笔者认为“垄断纠纷是否可仲裁第一案”的具体背景对江苏高院作出认定结论有重要影响,例如争议双方均为中国公司、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机构为中国境内仲裁机构、争议事项仅限于争议双方中国相应地区的经销事项等背景因素。概括言之,这个案件实质具体讨论的是,中国主体关于中国境内涉及反垄断的合同争议是否可以由中国仲裁机构管辖的问题。
在前述基础上,江苏高院虽然意识到欧美一些国家已经不再基于公共政策考虑将反垄断争议排除出仲裁事项范围,但仍然基于目前中国反垄断执法及司法尚未形成成熟经验的实际情况,综合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考虑,认定目前中国垄断纠纷不可仲裁。
具有涉外因素的反垄断争议中,不应当然否定仲裁条款的有效性而排除仲裁管辖。与前述“垄断纠纷是否可仲裁第一案”中争议主要限于国内主体不同,实践中,大量主体之间围绕合同产生的反垄断争议具有涉外因素。如争议双方一方涉外,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机构为境外仲裁机构,适用的准据法可能也是外国法律;争议事项可能也不限于一国境内,而是牵涉全球多个国家或地区,往往也更为复杂。
在此情况下,比较明显的是,相关境外仲裁机构在处理反垄断民事争议方面已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那么中国目前反垄断执法和司法的客观实际对于判断涉外垄断争议是否可仲裁的影响就不再那么重要。

HAN GUIZHEN
天元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Senior Associate
Tian Yuan Law Firm
关于公共政策角度,从欧美的司法实践来看,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85年在三菱汽车公司案中确认国际领域反垄断争议具有可仲裁性的原则以来,公共政策对判断垄断纠纷尤其是涉外垄断纠纷是否可仲裁的限制越来越少。中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公共政策的适用也日益审慎,不仅在不予承认和执行境外仲裁裁决时鲜少适用“公共政策”理由,而且更多强调从可能产生的结果方面客观分析是否存在会对中国法律秩序产生破坏,不会泛泛采用“公共政策”说辞。
可见,在具有涉外因素的垄断争议中,需要考虑和分析的因素更为复杂,公共政策、公共利益和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解决也需要更多平衡。因此,江苏高院关于“垄断纠纷不可仲裁”的认定结论能否当然在涉外垄断争议中适用就值得商榷。
涉外因素的反垄断争议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可能更有利于争议全面解决。在中国提起反垄断民事争议的请求权基础在于《反垄断法》第五十条,该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可见,中国平等主体间因合同产生的反垄断争议本质上仍属于具有财产属性与私权属性的民事争议,双方之间争议的解决虽然可能涉及相应国家和地区的竞争秩序和消费者福祉,但从争议核心来说更多体现为双方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
因此,过多强调一国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可能会导致涉外反垄断争议中双方的争议被人为割裂,不利于争议有效率地全面解决。(以华为诉IDC案为例,尽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了3G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的中国费率,但双方就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的全球许可事宜,仍最终由约定仲裁机构全面解决。)由双方选定的仲裁机构一并对双方围绕合同产生的争议全面解决,也可能较双方在多国各起诉讼碎片化解决争议更为效率。
综上,在我国当前立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垄断纠纷的可仲裁性的情况下,江苏省高院认定垄断纠纷不可仲裁不宜作为普适性结论,具体平等主体间的涉外垄断纠纷是否可以仲裁,仍需要进行个案分析。
黄伟是天元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兼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反垄断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国际商会竞争委员会首任中国专家,其联系方式为电话 +86 10 5776 3888 或电邮 hwei@tylaw.com.cn
韩桂珍是天元律师事务所反垄断团队资深律师。其联系方式为电话 +86 10 5776 3888 或电邮 hangz@tylaw.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