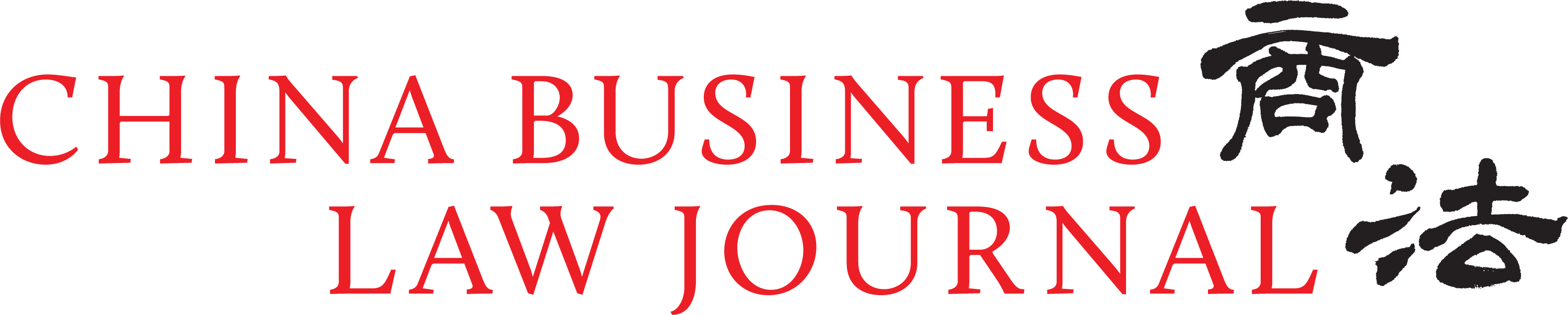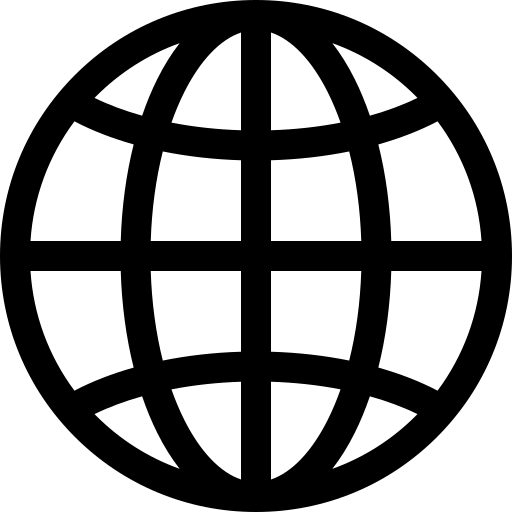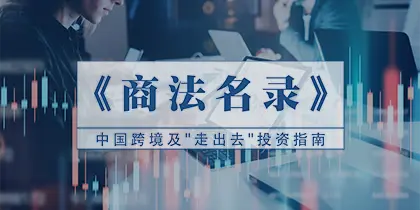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增加了“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由,该规定亦同日实施。2021年11月1日生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个人权利及信息处理者义务、法律责任等进行了全面规定,建立起全球范围内较为严格的立法框架。至此,由《刑法》《民法典》《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范组成的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已构建完成。

高级合伙人
中咨律师事务所
以此为基础,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视行为类型及情节严重程度,会受到刑罚制裁或行政处罚;检察机关、消费者组织等可针对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的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除了以上公权利救济途径外,个人也可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诉讼。
在法律体系得以完善前,中国的数字经济已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及规模发展壮大。受益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及超大规模市场,基于个人信息大数据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出现,已孕育出了多个处理海量个人信息的平台企业。部分平台企业通过“数据+算法+平台规则”形成交易优势,损害消费者权益及妨碍公平竞争屡有发生。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之后,个人信息处理者尤其是平台企业,不仅面临着监管机构的纠正和规范,还面临着个人信息保护民事诉讼的追责。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纠纷虽时有发生,但囿于立法的滞后,在《民法典》颁布前较长时间内,相关纠纷多以名誉权、隐私权作为构成要件进行审理。不过,在《民法典》颁布前夕,法院判决开始将个人信息与隐私权区别对待,将个人信息作为独立法益进行保护。
当前更多数量的“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件出现,并呈现出如下特点:
当事人及诉讼目的多样化。部分原告本身为律师、法学学生等法律专业群体,针对某些互联网服务平台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提出侵权指控,如针对“微信读书”“抖音”提出的个人信息保护案件。部分原告基于自身个人信息被不当采集、非法泄露或错误处理,针对电信企业、航空公司、金融机构提出诉讼。其中,涉及金融机构征信记录的诉讼案件数量,在个人信息保护案件中占比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出现了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提起的职业索赔诉讼。
侵权认定考虑个人及公共利益的平衡。在已有案例中,法院在个人信息处理合法性的认定中,尤其在涉及大数据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认定中,不仅考虑个人授权及“合法、正当、必要”原则,而且考虑“社会经济发展”“信息自由流动”等公共利益。《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基于公共利益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进行了限缩规定,可以预见,在将来的个人信息保护诉讼中,法院将采取更为严格的标准,对个人信息商业使用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适用人格权保护的救济手段。个人信息属于人格权益,因此,侵犯个人信息适用侵犯人格权的民事责任承担形式,即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
损害后果亦是判决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及金额的考虑因素。当前法院普遍不支持高额金钱赔偿,但普遍支持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及偿付维权合理费用。部分案件虽认定侵权,但因损害后果未达一定程度,而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虽然个人信息保护案件的赔偿金额不高,但可能对平台原有的信息处理规则甚至商业模式产生重大影响。部分案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法院的裁判不仅迫使相关平台改进相关规则或作法,也促进了后续个人信息保护配套规范的完善。
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之前,已有部分案例从收集证据的能力及可能性出发,认定信息处理者应对没有泄露个人信息进行举证,否则应承担侵权责任。《个人信息保护法》则正式确立了侵犯个人信息的过错推定原则,即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
综上,随着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构建完成,个人信息保护诉讼呈现数量增加、类型多样化的趋势。更为严格及全面的法律规范,给予了个人信息更大的保护力度,同时对互联网平台、电信企业、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处理大量个人信息的主体提出了更高的合规要求。
李春谊是中咨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他的联系方式是电话+86 10 6625 6419以及电邮lcy@zhongzi.com.cn